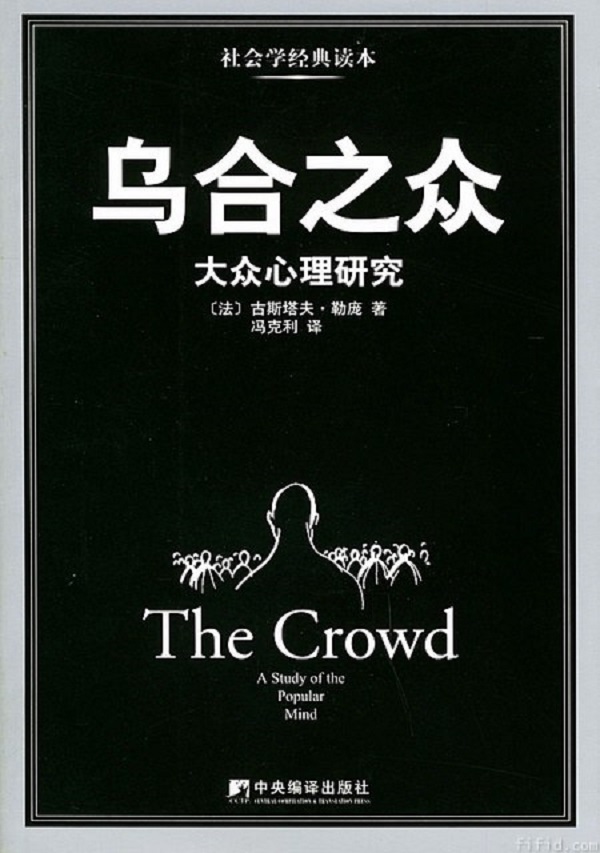
百部人文经典之《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索书号:C912.6/L077
馆藏地址: 三楼综合书库
摘要:
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
孤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 这种冲动总是极为强烈,因此个人利益,甚至保存生命的利益,也难以支配它们。刺激群体的因素多种多样,群体总是屈从于这些刺激,因此它也极为多变。 对群体中的个人来说,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
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他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
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
群体随时会反抗软弱可欺者,对强权低声下气。如果强权时断时续,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左右,它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卑躬屈膝。 群体强烈地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此很容易屈从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对它们撒手不管,他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倦,本能地变成奴才。
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 20本滔滔不绝的长篇论证——它们总是认真思考的产物——还不如几句能够对它试图说服的头脑有号召力的话。 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它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
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也都把群众的想象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它作对而进行统治。 如何影响群众的想象力呢?这里我们只需说明,要想掌握这种本领,万万不可求助与智力或推理,也就是说,绝对不可以采用论证的方式。 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
这种感情有着十分简单的特点,比如对想象中的某个高高在上者的崇拜,对生命赖以存在的某种力量的畏惧,盲目服从它的命令,没有能力对其信条展开讨论,传播这种信条的愿望,倾向于把不接受它们的任何人视为仇敌。这种感情所涉及的不管是一个看不见的上帝,一具木头或石头偶像,还是某个英雄或政治观念,只要它具有上述特点,它便总是有着宗教的本质。
法国的群体特别看重平等,英国的群体则特别看重自由。 辩护人不必让陪审团的每个人都接受他的观点,他只争取那些左右着普遍观点的灵魂人物即可。 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全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大都是教授或学者,然而他们何曾就哪个普遍问题——贸易保护、双本位制等等——取得过一致意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学问不过是我们的普遍无知的一种十分弱化了的形式。在社会问题上,由于未知的因素数量众多,从本质上说人们的无知没有什么两样。
群体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中间寻找自己的主子,他们永远需要这种人物。 赫伯特·斯宾塞在一本很久以前的著作中就曾指出,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
支配着大众的,永远是榜样,而不是论证。每个时期,无意识的群体都会模仿少数有个性的人。但是这些特立独行的人还是会默认普遍的观念。他们要不这样做的话,模仿他们就会变得异常困难,他们的影响力也会因此缩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于超前的人,对于自己的时代一般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两者有太严重的脱节
无论是独立的个体还是群体,一旦他们处于暗示影响的状态之下,那么他们的思考功能就会彻底丧失。从一个念头进入大脑到付诸行动,这期间没有任何的时间间隙,几乎是立即就变成了行动。 这就让我们看到了群体与冷静的个体之间的区别。 独立的个体——即使是处于被暗示状态之下,他的行动也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理由的。 这就是说,独立的个人即使是受到暗示,他也必须在暗示的内容与行动的结果之间找到直接性的关系,然后才有可能付诸行动。 而群体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群体所采取的行动与其思维逻辑产生了直接性的对立! 事实上,群体是极端排斥理性与逻辑的。
在群体之中,与无意识无关的任何理性、思维或逻辑统统都是不存在的。 如果你想给群体一个信服的理由,就必须记住这一点。 而事实上,群体所能接受的更多只是那种子虚乌有的神话与毫无逻辑的故事。除此之外,他们对一切都无法理解。 一些在只要稍具辨别能力的人听起来是那么荒诞无稽的神话与故事,却非常容易在群体之中产生并迅速流传。 群体之中极易流传神话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群体的极度轻信,也是事件的本身在人群中的想象经过了极为奇妙的曲解之后的效果。 此外,当群体过于长久地沉浸于这种虚幻的氛围之中的时候,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对群体无意识的创造物的质疑能力。
这不过是因为我们从原始时代继承了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它蛰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孤立的个人在生活中满足这种本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当他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时,因为很清楚不会受到惩罚,他便会彻底放纵这种本能,在生活中,我们不能向自己的同胞发泄这种破坏性本能,便把它发泄在动物身上。群体捕猎的热情与凶残,有着同样的根源。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表现出一种十分懦弱的残忍。不过在哲学家看来,这种残忍,与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猎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表现出的残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群体对强权俯首贴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他们认为那不过是软弱可欺的另一种形式。他们的同情心从不听命于作风温和的主子,而是只向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他们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雕像。不错,他们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但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他也变成了一介平民。他受到蔑视是因为他不再让人害怕。群体喜欢的英雄,永远像个凯撒。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
通常,一代人的经验对下一代人几乎没多少用处的。他们唯一的用处就是证明了,一种广泛的经验即使仅仅想成功动摇根植与群众心中的谬论,需要一代又一代重复的出现。
不可否认,文明是少部分智力超常的人的产物,他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点。 一种文明的伟大,如果仅仅依靠以人多势众自夸的低劣成员的选票,是不足以让人放心的。
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是有所欠缺的,因为它不敢做出过于慷慨的承诺,因为它不能撒谎。 群众从未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拂袖离去,倘若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凡是能向他们提供幻觉的,也能够很容易的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将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不存在任何引导意见的力量,再加上普遍信仰的毁灭, 其最终结果就是对一切秩序都存在着极端分歧的信念,并且使群众对于一切不明确触及他们直接利益的事情,越来越不关心。
一种信念开始衰亡的确切时刻很容易辨认——这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的时刻。一切普遍信念不过是一种虚构,它唯一的生存条件就是它不能受到审察。 不过,即使当一种信念已经摇摇欲坠时,根据它建立起来的制度仍会保持其力量,消失得十分缓慢。最后,当信念的余威尽失时,建立于其上的一切很快也会开始衰亡。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在没有下决心破坏其全部文明因素的情况下转变它的信仰。这个民族会继续这一转变过程,直到停下脚步接受一种新的普遍信念为止,在此之前它会一直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中。普遍信念是文明不可缺少的柱石,它们决定着各种思想倾向。只有它们能够激发信仰并形成责任意识。
假如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它的文学、艺术和不朽之作,我们对以往时代的真相便一无所知。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开动脑筋考虑起自己的眼前利益,我们这个星球上根本就不会成长出文明,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 侵略者的权力和国家的威力,便是建立在群体的想象力的。在领导群体时,尤其要在这种想象力上狠下工夫。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崛起,都是因为对群体的想象力产生强烈影响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 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