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满心承认常规生活的社会价值,也看到了它井然有序的幸福。但我的血液里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人生是更为狂放不羁的旅途。
那些慷慨激昂的人自以为他们说的话是前人闻所未闻的,殊不知此类豪言壮语早已被说过上百遍,而且连说话的腔调也大同小异。钟摆甩过去又荡回来。这个过程永远往复无休。
我忘记是谁曾经说过,每天做两件自己讨厌的事对灵魂是有好处的。
其实很多人的面目都是这么模糊的,他们生活在社会有机体之内,又跳不出体制的窠臼,慢慢的也就泯然众人矣。他们很像身体里的细胞,重要是很重要,但只要是健康正常的细胞,就会被巨大的总体吞没而显露不出来。
但如果罪人对他犯下的罪行直认不讳,想劝他洗心革面的人还能有什么话说呢?
只有诗人或圣徒才会坚定不移地相信在沥青路上浇水能种出百合花来。
你怎么会认为美,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像沙滩上的石头,随便哪个满不在乎的过路人都能捡起来呢?
编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如果超群出众的人物在其生涯中遇到某些令人感到惊奇或者神秘的事情,人们就会及其贪婪地抓住不放,将其演绎成一段传说,然后狂热地深信不疑。这是人们对平淡生活提出的浪漫抗议。传说里的轶事变成了英雄晋升不朽境界的最可靠的通行证。
我总觉得有些人没有出生在正确的地方。偶然的命运将他们丢在特定的环境里,但他们总是对某个不知在何处的家乡念念不忘。他们是生身之地的过客,从孩提时代就熟悉的林荫小径,或者曾在其中玩耍过的热闹街道,都无非是人生路上的驿站。他们始终把亲友视为陌路,对生平仅见的环境毫无感情。也许正是这种疏离感推动他们远走高飞,去寻找某种永恒的东西,某片能让他们眷恋的土地。
每当有人做了不合常理的事情,他的熟人就会替他设想出最离奇的动机。
有时候,人会偶然造访某个地方,却神秘地感到这里就是他的归宿,这里就是他朝思暮想的故乡,尽管周边的环境他从未见过,尽管当地的居民他素未谋面,他却愿意安顿下来,仿佛这些都是他生来便已熟知的。
在这里他的心终于不在躁动。
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我们不觉得由于爱惜羽毛而对离经叛道的行为保持沉默是虚伪的表现。
艺术家——画家、诗人或音乐家,以其崇高的、美好的创作装点世界,满足人们对美的感知。不过其创造性与性本能相似,都带有粗野狂放的一面。在将其杰作展示给世人之时,艺术家也将自身更加非凡的天赋呈现于世人面前。探究艺术家的秘密有些像阅读侦探小说。它是一个谜,如鸿蒙宇宙一般,妙就妙在无解。
他们记起了自己当初也曾经把一代高踞宝座的人践踏在脚下,也正是这样大喊大叫、傲慢不逊;他们预见到这些高举火把的勇士们有朝一日同样也要让位于他人。谁说的话也不能算最后拍板。
要是你要伤害一个人,那就伤的深点。这样才有时间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
皈依可以以许多形态出现,也可以经由许多途径实现。一些人需要通过激烈的灾难,犹如凶猛的洪流可以把石头撞得粉碎;对于另一些人,它渐次到来,好像不断的水滴终将石头洞穿。斯特里克兰则兼有执迷着的一意孤行与使徒的凶狠蛮横。
不在乎别人的意见,根本不可能。早晚,你身上的人性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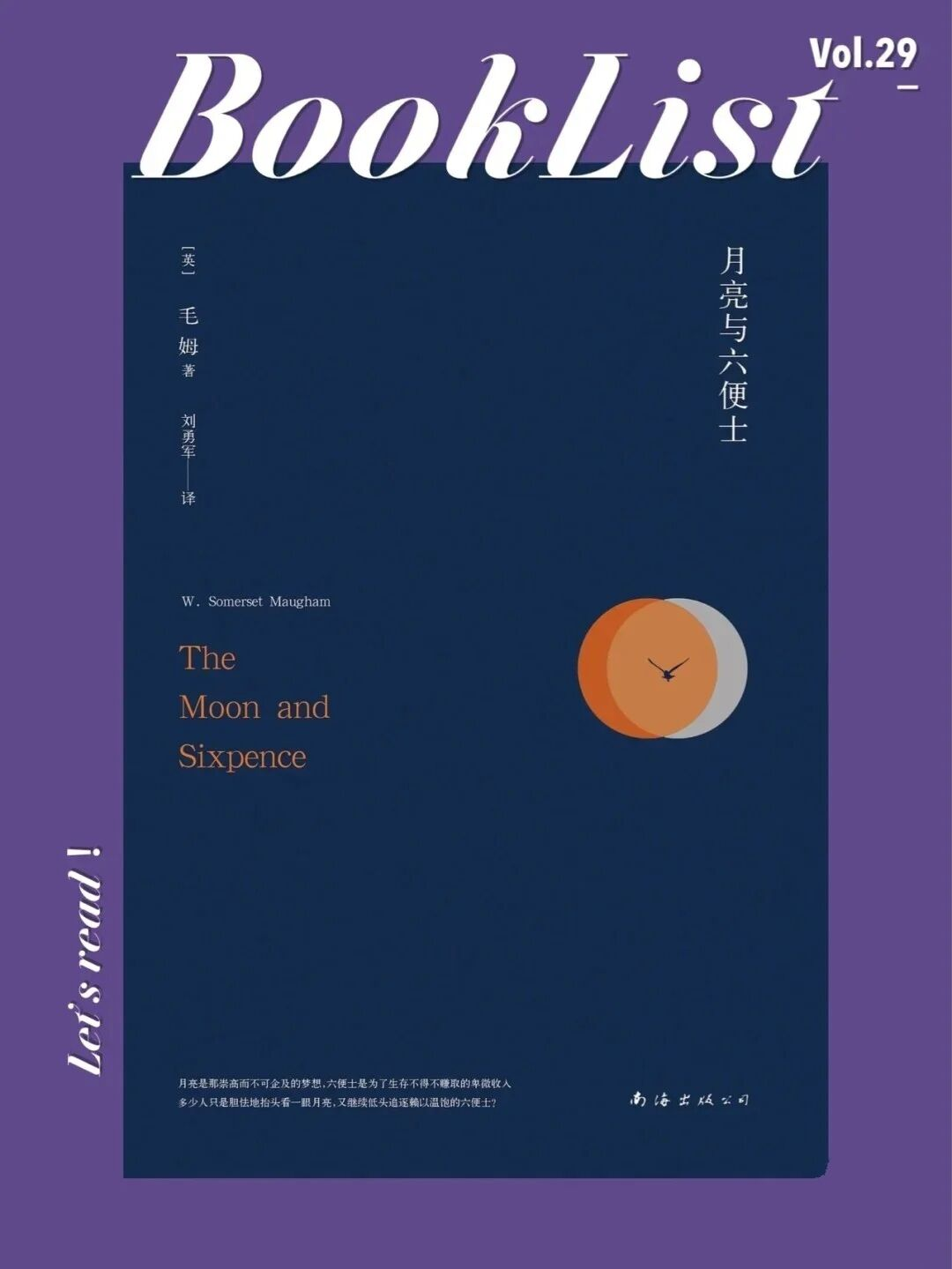
来源:威廉·萨默赛特·毛姆《月亮与六便士》
学校:威尼斯886699
院部:工商管理学院
班级:19财管1班
学号:20190441101
姓名:孙娟